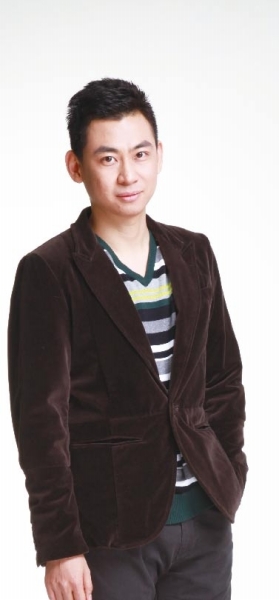文 | 蔡娴
借着三拓旗剧团“1、2、3戏剧季”的机会,时隔两年后,青年戏剧导演兼剧团创建人赵淼再次带着他的“哀伤的幽默”和“精彩的想象”来到了上海。如果说,2010年的《壹光年》仅是一次出场亮相,赵淼用他的形体戏剧惊艳了沪上观众,那么,这次包括《壹光年》《飞要爱》《九种时刻》及2012年在阿维尼翁戏剧节、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上大获好评的新作《水生》在内的四部戏剧轮番登场,这出戏才真正演到了最精彩的部分。
“如果我给出的指令是大象,你就要用两只手做出个象鼻子来,左右两边的人也不能闲着,要组合成大象的耳朵。”采访当天,记者跟赵淼的初次接触不是起于采访,而是以一个观众体验者的身份被他指导排戏。他不会用任何的台词来约束你,只是不断引导你尽可能地做出到位的动作和表情,用肢体语言来进行表演,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定格场景,通过他的巧思、组合后就是一出别具意味的小故事。
更有意思的是,和记者同组搭戏的是赵淼的堂哥,毕业于中戏的演员唐旭,可以说,正是他将赵淼领进了戏剧的门。“上高中的时候,我会去中戏看我哥他们演戏,就是因为看了他们的表演,我才知道什么是戏剧,而且我每个礼拜都会去他们学校打篮球,所以,我知道的第一所大学就是他的大学——中央戏剧学院。”
1996年,在戏剧的耳濡目染下,还是高中生的赵淼就和六七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自娱自乐的小剧社,也就是三拓旗的雏形,“那是在高一第一学期的冬天,马上要过圣诞节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为了庆祝还特地一起去吃了顿麻辣烫。”虽然一晃16载,但这意义非凡的一天至今对赵淼来说仍是历历在目。
考了3年的中戏,扛了16年的“三拓旗”,剧团之于他,可以说是梦想的起点,戏剧则是他坚守的理由。当年三拓旗的创始班底早就各奔前程,唯有赵淼仍守护着这棵梦想的萌芽,并细心浇灌、培育。如今的三拓旗也一路从最初中学生的小打小闹,到颇有人气的大学剧社,再到如今独树一帜的专业戏剧团队。三拓旗各个阶段的演变,其实也就是赵淼戏剧之路的进化过程,不断地寻求转变。
对话赵淼
TY: Touch Youth ZM: 赵淼
邂逅形体戏剧
TY:小时候参演过《爱情麻辣烫》、《大明宫词》等,可以说你是童星出身,但为什么最后读了导演系而不是表演系?
ZM:这个特别有意思。拍《大明宫词》时,有一场戏是我被杀死,上一个镜头水桶是立着的,然后到我演那场戏的时候,导演喊“预备”,我说“停!这水桶怎么倒了?”连导演都嫌我特别爱操心。因为这都不是我的工作,但我就是会留意到这些,爱琢磨,而且每次排完戏我都会跑到导演那边去看镜头画面。后来就有朋友建议我说,其实你的很多想法是导演思维,更适合去考导演系。
TY:“三拓旗”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ZM:就是“三人成众,拓展为旗”的意思,“三人成众”其实是一种方法,你要善用团队的力量,而“拓展为旗”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反对的是跟着别人的脚步,做雷同的东西,希望能有一个探索的东西,有所不同,哪怕它是错的。
TY:什么是“错的”?
ZM:就是你排完的东西自己都不想看。读了大学之后,有了一定的概念,起码你能知道这东西不对,但之前连什么是错的都不知道。那时候还是比较茫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做了很多的东西却发现不是特别能打动自己,直到遇上了形体剧,你就觉得,是,就是它!你等的东西就是它了!
TY:怎么会接触到形体戏剧?
ZM: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英国有两个剧团来中戏参加“爱丁堡艺术节”,一个叫《三个黑故事》,一个叫《红舞鞋》。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形体剧,我只知道这个戏是用形体在演,没有台词。那时我就觉得特别好玩,很有意思,又真诚,我觉得真诚是很重要的。他们还在学校里讲课,说当你扮演一个儿童的时候,可能需要咬自己的皮鞋,对一般人来说会有点困难,但你是演员,你就一定要咬,不要有所顾忌。这就是在教我们一定要真诚地去面对。看了他们的戏以后,我就去研究这到底是什么?是哑剧还是默剧?但是后来发现其实都不是,而是叫形体戏剧,是有很明确归类的剧种。
TY:很多人会从形体戏剧中看到话剧、舞台剧、哑剧等许多剧种的影子,它们之间有怎么样的关系?
ZM:形体剧其实将很多剧种都综合在了一起,在这些戏剧的基础上再发展,使形体剧的表现方式变得很丰富。早在1956年,欧洲的形体戏剧学校就开始教现代舞、默剧、哑剧,他们各个剧种的课都会上,就是告诉你怎么用身体表现出无限的东西。
寻找肢体的可能
TY:形体戏剧导师雅克·勒考克对你的影响很深,你曾经说,他的形体戏剧,让你更加清楚什么是残酷戏剧,什么是质朴戏剧,那你觉得自己的戏属于哪一类?
ZM:质朴类吧。所谓残酷,其实指的是它的观念比较残酷,追求极致的东西。我们也追求极致,但要分几步走。如果上来就追求极致的话,很多观众就会被我们甩掉。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引导他,因为十年你坚持做一件事情,观众会明白,他们也在成长。我们第一次演《6:3》的时候,有些观众就骂,就吵,现在不同了,所以它是一个“革命”的道路,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去引导他们。所谓质朴,不只是说没有道具,或者舞台不精致,而是要使用最简洁的方式。我坚持的一点是:当其他很多东西都省略的时候,我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演员变得更真诚,因为戏剧最中心的部分就是演员的表演。
TY:形体戏剧与传统戏剧相比有哪些优势?
ZM:第一点,形体戏剧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用最直观、最简洁的方式来表现。就像我们之前排的短剧,只要4个定格场景,不超过50秒就可以把人类整个历程表现出来。第二点,它会大量地去调动观众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人生或者我们还不懂什么是人生的话,我们是很难看懂的。但当我们遭遇过亲情、爱情、友情,每个人都有故事之后,再来看,一下子就会明白了。因为,它和观众的互动是最强烈的,观众笑也好,观众被打动也好,一定不只是舞台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舞台上发生的东西让他想到了自己。第三点,它更容易被观众看懂,我们出国演出或是演儿童剧的话,都不用字幕,也不用讲解,因为孩子们是最直接的,外国人看都就不需要什么字幕,那我们国内的人看就更没有问题了。我们现在的几部戏都还是比较具象的,很容易让人看得懂。
TY:你曾在受访时表达过,在形体戏剧创作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文本以及观众的接受力。怎么解决?
ZM:就是引导观众去理解。像台词最多的戏《飞要爱》,全剧台词不超过八百个字,然后到《壹光年》,全剧台词不过三百个字,甚至到《九种时刻》,我们一句台词都没有了,再然后到《水生》的时候连表情也没有了。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发展的整个的过程。我们其实最终的目标是想让观众看到不说话的戏。
TY:如果观众看不懂怎么办?
ZM:我们希望观众能琢磨,如果看不懂,他走在路上会思考“为什么会这么演呢?”,百分百都懂了,那不好玩。他可以看不懂,也不用看懂,一个戏能明白50%就足够了,剩下的50%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去想。
发乎于情
TY:有观众形容你们的戏带来的感觉是“直指人心的动容”,你在排戏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发掘出一些“抓人”的细节?
ZM:我们排《壹光年》的时候,故事讲的是一个单亲家庭,我本人并不是,但演员中有人是,为了让这个故事更真实,我们让所有人都做生活讲述,每个人都要无所保留,真诚地跟我们交流。所以,在教这段戏的时候,发觉我们的演员对故事、对人物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从而去做一些来源于真实生活的修正。
TY:你除了当导演,还是编剧,你所编排的戏,故事与故事之间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还是会埋下一些暗线作关联?
ZM:我们不管什么戏,都有一个核心的内容——亲情。这是我们自己偷偷藏的彩蛋,你仔细看会发现,其实所有故事里都有“水”,“上善若水”,但要是没有好好引导的话,它会害人。比如说,去年7月21日北京下暴雨,在高速公路上淹死了70多人,这简直不可想象。我们当时在法国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在那个断桥边,看着那么美的“水”,都不能理解,水可以变成恶魔,但是什么让它变成恶魔呢?是人,是人性“恶”的东西。除此之外,每部戏也都会有一个老人。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我们自己也会有老的一天,当我们关注到老人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关注到自己,因为老人面对的是死亡,只有我们开始直面死亡的时候,才能知道什么是生命。
TY:接下来的创作在风格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ZM:我们的戏剧会更加的风格化。我们会更加关注到观众的欣赏习惯,比如《飞要爱》和《壹光年》,他们希望说点话再加上形体表演,但到《九种时刻》,就已经开始极致化,没有任何语言,没有表情。再往后的话,我们会让风格更现代,去反应当代年轻人是怎样看待情感的。